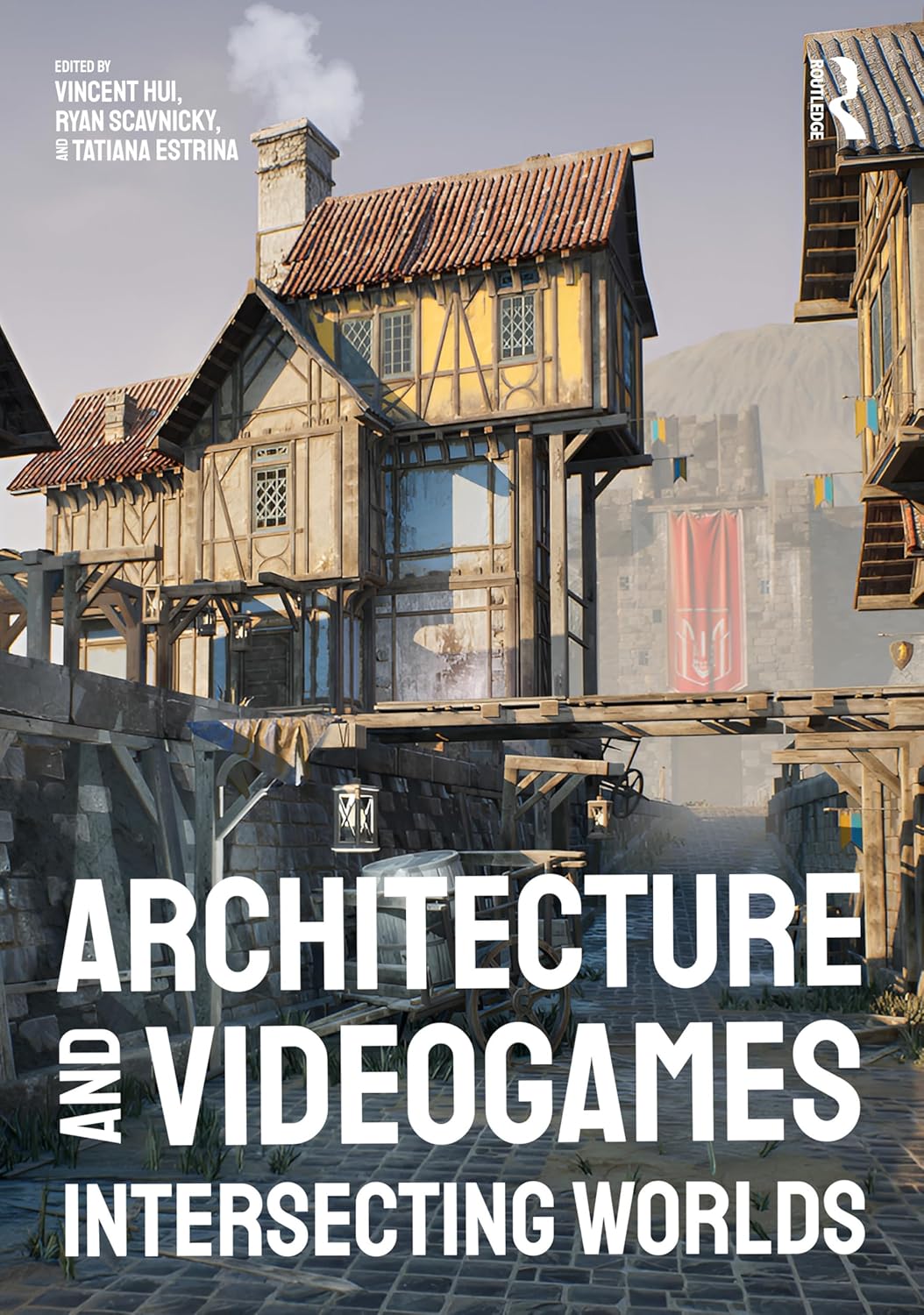
《建筑与电子游戏:交织的世界》(Architecture and Videogames: Intersecting Worlds),将建筑与游戏设计结合在一起,序言写道:“本书从建筑的视角开始研究电子游戏所创造和培育的虚拟空间”。探讨了建筑学与电子游戏设计这两个领域日益紧密的交融,通过数字技术相互连接,共同塑造着我们对空间的理解、体验与创造。本书揭示了虚拟空间如何通过建筑学的视角被生产和培育,并从学术研究与实践案例出发,分析了这种交叉融合的核心内涵。
电子游戏的空间就是建筑思维的空间。毕竟,许多建筑最初都是以3D数字模型的形式构思和设计的,因此,将电子游戏视为建筑作品,只需在核心建筑理念的应用上稍作调整,便可理解。这拓展了建筑与公众想象力的边界,并让我们得以一窥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融合的未来空间设计,在这两个充满活力的领域交汇之处,为新的家庭生活和其他潜在世界打开大门。

虚拟空间作为建筑思维的延伸
- 电子游戏空间本质上是建筑思维的体现。建筑通常始于3D数字模型的概念化与设计,因此将电子游戏作为建筑作品审视,只需对核心建筑理念的应用稍作调整。
- 这种融合拓展了建筑学与公众想象的边界,预示着一个虚拟与物理空间交织的未来,为新的居住模式(新家庭性)和潜在世界开辟道路。
- 理解建筑在游戏环境中的作用,必须考量社会对“游戏”的渴望,以评估其潜在的空间与文化效应。游戏中的建筑如同角色,具有鲜明个性(如《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中的格鲁德冰屋),并可通过建筑理论(如Jay Appleton的“前景-庇护”理论)进行图解分析。将虚拟建筑(如冰屋)转译为现实空间(如加油站),能揭示游戏与现实建筑、玩家与怪物/玩家与工人之间空间冲突的惊人相似性。
沉浸式生态系统与社会容器
- 随着电子游戏日益沉浸化与主流化,其空间已从单纯的3D环境演变为包含社会维度的完整生态系统。
- 游戏空间不仅包含玩家互动的虚拟模型与建筑,更延伸至围绕游戏休闲时间和空间的物理与社会“容器”。这些容器形态多样:
- 全球联机玩家共享的公寓沙发;
- 旅行者边候机边游玩的掌机;
- 拥有数千观众的Twitch聊天室。
- 每个容器都提供两层振荡的信息流(如游戏内HUD界面与现实环境信息)。虚拟建筑的创造依赖于理解这些混合机制与社会互动的层级化结构,它们被精心编排成有意的空间体验。
与卫星图.jpg)
虚拟愿景建筑:纸上建筑的数字化新生
- 任何模拟世界都关联着已知世界。建筑学历史上通过“纸上建筑”(未建成的方案)来评论当下世界并构想变革。如丹尼尔·伯纳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等人所示,建筑具有模拟新现实并说服人们其可行性的力量。
- 愿景建筑(Visionary Architecture)是纸上建筑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主动承认其不可行性,以批判性地审视世界状况。莱比乌斯·伍兹(Lebbeus Woods)定义了其三个核心属性:
- 针对特定城市状况提出新的设计原则。
- 设计具有全局性。
- 发明新的建筑类型。
- 勒·柯布西耶的《伏瓦生规划》 (1925): 为缓解巴黎拥挤提出的激进方案(拆除市中心建摩天楼与机场跑道),虽被拒,但其关于高密度、公平居住的核心理念(如Herman Jessor的Co-Op City项目)与大规模历史核心区清除的潜在危害(如辛辛那提Over-the-Rhine社区悲剧)引发了深远讨论。
- “多姆吉拉”宿舍提案 (2021): 查理·芒格为UCSB设计的无窗宿舍引发公众强烈反对迫使项目取消,体现了“纸上建筑”揭示社会价值观与居住条件底线的力量——愿景若背离大众接受的生存条件极限,将激发社会抵制。
- 游戏作为变革现实空间的催化剂:
- 《Pokemon Go》现象 (2016): 这款混合现实游戏通过“PokeStops”(常设于市政建筑、图书馆、公园)将玩家大量吸引至公共空间,显著激活了市民空间。本地商家(如洛杉矶酒吧)利用游戏内道具“诱饵”结合现实优惠吸引顾客,反之则面临客流流失,展示了游戏机制如何即时重塑建成环境的经济与社交模式。
- 虚拟愿景建筑的更新原则: 鉴于建筑与游戏创作均需多方协作,伍兹的三原则可更新为:
- 项目提出关于人际互动与行为的新原则。
- 设计具有全局性。
- 发明新的空间类型。
伦理考量:空间、行为与美学
- 评判游戏作为建筑的一大挑战是,体验其空间常需进行暴L或M杀行为。这引发了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关于“搁置道德判断以评估艺术美学”的论述与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在建筑中M杀才能真正欣赏空间”的悖论之间的张力。
- 屈米的论点核心在于:定义空间的是其中发生的行为,而非围合它的墙体。在此框架下,虚拟环境中培育的假装游戏、社区建设和休闲行为,其“颠覆性”足以满足屈米对“定义空间的行为”的要求。
- 非暴力叙事游戏(如《风之旅人》、《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糖豆人》)证明了虚拟媒介可提供纯粹的美学体验,并通过独特机制(如限制沟通、展示修复性生态、测试身体公平性)探索行为标准、生态愿景与身体认知,实现了作为社会批判的虚拟愿景建筑理念。正如伍兹所言,其作品旨在探索“摆脱传统限制后世界可能的样子”。
构建意义:空间、时间与劳动印记
- 为使虚拟空间容纳丰富活动,须赋予其深刻的文化价值。游戏设计师创造意义的手段(时间流逝、玩家/社区参与)呼应了历史建筑理论。
- 拉斯金的“生命之灯”理论 (1849) 的当代诠释:
- 建筑应显露人工痕迹,传递建造者的技艺与历史。这类似于玩家改变游戏环境带来的互动感。
- 关键区别在于:拉斯金强调的是建造者(builder),而非居住者(homeowner)。在游戏开发行业劳动条件常受诟病的背景下,游戏中的独特世界构建细节和“彩蛋”让玩家得以亲近一种新型“工艺”,预示未来建筑中劳动者/工匠能留下个人印记供居住者体验。
- 拉斯金认为“所谓的修复是最恶劣的破坏”,建筑的历史与岁月痕迹即其灵魂。玩家在游戏环境中留下的印记(如在《塞尔达传说》家中展示武器)与现实童年家中墙上的涂鸦,都是通过空间介入创造的特定共享文化体验。
- 时间印记与怀旧价值: 游戏机制(物品永久损毁、玻璃破碎不可修复)或重制经典地图(《光环》Blood Gulch、《堡垒之夜》初版地图)的成功,反映了人们对空间历史痕迹的情感依恋。当代网络迷因文化(如对《托尼霍克滑板》中Woodland Hills仓库的怀念)更印证了特定虚拟空间与家庭休闲舒适感的紧密关联,体现了对往昔的渴望。
超越建筑师:协作、话语权与混合生活
- 《堡垒之夜》的启示: 经典地图回归吸引310万玩家同时在线的盛况(远超平日40万),其规模堪比人类史上最大规模集会。这突显了虚拟空间聚集力的巨大潜力,并引发思考:若将游戏《控制》(设定于曼哈顿33 Thomas Street)的空间与所有玩家活动可视化,将是何等景象。
- 对“无建筑师建筑”的批判性审视:
- 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1964年MoMA展览“无建筑师建筑”旨在挑战建筑史经典,推崇“乡土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质疑建筑师对生活问题的专断。然而,展览将乡土结构剥离语境置于白墙之上,意图供“专业”观众汲取灵感进行新创作,反而强化了其鄙视的“声望循环”,并因特定受众导致对作品的“恋物化”(fetishization),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
- 话语权的重新定位: Andres Souto的《盛大之旅》(El Grand Tour)视频通过展示SketchUp Warehouse上的业余创作,颠倒了传统“大师发现无名天才”的叙事,视业余者为真正的天才。这指向了建筑应对作者身份与乡土挑战的新路径——吉尔·斯托纳(Jill Stoner)的《迈向小型建筑》提倡“解构权力结构,自下而上解放”。
- 乡土的核心价值: 对乡土建筑的借鉴应超越形式恋物,关注其如何创造和培育共享的家庭意象。任天堂Switch广告展示两兄弟在线共玩1997年游戏《黄金眼007》,唤起童年卧室的共享休闲记忆,揭示了虚拟空间作为家庭空间延伸的深刻意义。
- 混合家庭与教学实践:
- 建筑师/教师Ryan Scavnicky受Viviane Schwarz启发(在《荒野大镖客》营地开编辑会议),在2020年使用虚拟平台Sansar进行远程课业指导,并创新性地以Twitch“聊天扮演陪审团”形式进行终期评图。这使建筑评审向更广泛的公众开放,同时体验了一种新型共享家庭空间(利用游戏虚拟空间进行教学)。
通过微调核心理念,建筑中的“家庭”正从封闭单元向渗入共享虚拟容器的方向转变。
Black-Myth-Wukongun.jpg)
电子游戏与建筑的融合呈现出一幅空间设计、社会影响与文化意义交织的复杂图景。电子游戏已进化为沉浸式生态系统,超越数字环境成为堪比实体建筑的文化载体。它们塑造行为、反映社会规范、改造物理空间,消融了虚拟与现实建筑间的假定边界。虚拟愿景建筑(Virtual Visionary Architecture)的概念已然浮现,它预示着反映社会多元声音的协作设计与参与式体验。无论是围绕客厅游戏机的亲密聚会,还是通过在线平台与全球社区的互动,玩家栖居于多样化的空间语境中,丰富着自身体验。理解这些混合的家庭机制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性,对于通过虚拟世界设计这一共享文化想象的新项目来重塑建筑学科至关重要。